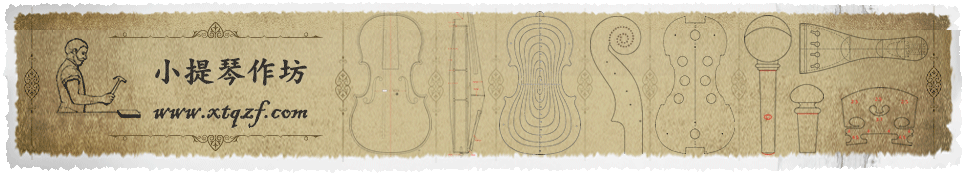大提琴演奏家卡萨尔斯的教学方式

当代所有的大提琴家都得感谢卡萨尔斯,因为他在二十世纪初改革了大提琴的演奏技术。他发明用很徽妙的方法来扩展手指的活动范围,和使左手的技巧更有活力,使左手从某种固定不变的和刻板的姿势中解放出来。他还使运弓的技巧更加自由。在卡萨尔斯之前,甚至教学生在腋下夹一本书来练习拉琴,以此来帮助做到一种固定不变的持弓姿势。卡萨尔斯立即理解到右手应该从这种勉强的姿势中解放出来。
卡萨尔斯的影响所以是非凡的,还因为他的长寿。他活跃的艺术家生涯经历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在这漫长的时期中,他的演奏、教学,还必须指出,还有他的指挥,给好几代大提琴家们传授了知识和见解。
在他一生的最后阶段,他居住在波多黎各,从地理上来讲是与美国非常接近,虽然他经常到欧洲和以色列去演出,但是他对年青一代演奏家的直接影响可以在美国最强烈地感受到。因为有十二年他每年都到马尔博罗去指挥,而且他在波多黎各的‘节日管弦乐团’是极好的。克利夫兰、芝加哥和其他一些第一流的管弦乐团的声部长全来作为一般的演奏员坐在后面的谱台上演奏,仅仅是为了可以为卡萨尔斯演奏和向他学习。
在他的专家大课或在他指挥管弦乐队,这像是给整个乐队上大课—的时候,人们可以感觉到人的精神和艺术技巧的明显的统一。这种统一性在目前的音乐界中是很少见到的。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他具备极有深度的人性和感情,同时又具有作为音乐家的伟大性。这两种特性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种辐射性能—他极为朴实地把一些非常热情和有深度的东西传送给听众。
卡萨尔斯在课上是用两种标准来教授的。他通常在开始评论一个他还不太了解的学生之前会要求演奏一首乐曲中很长的一个片段。然后他会说出几个很明确的意见,一般是关于技巧性的问题,这些意见就像设立的路标一样让学生去追求,如揉弦过分、指法不干净、音准差或是弓子的压力木大。对这类问题他指出得很快和很果断。在这方面对每个学生都区别对待。举例来说,如果学生在用弓方面太胆怯,卡萨尔斯会用几乎像是爆炸似的力量非常突然地下弓演奏,来对比出他能做到的程度。另一方面,如果学生在弓子上使用的压力太大,使琴弦无法自由的振动,卡萨尔斯则示范如何能演奏得轻巧和优美。他很巧妙地不去给所有的学生一套刻板的规则而是用许多不词的方法去教他劝。你必须皆加许多次课和听许多学生给他演奏,你才能得到他对大提琴教学的概念和理解不僵化和不教条是也的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卡萨尔斯授课中的另一个标准是音乐方面的。他会自己逐句述句地演奏一首乐曲。我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他的解释演奏的绝对的原则之一是:在演奏中要找出乐句的构思。对卡萨尔斯来说,每一乐句都是有活生生的形状,有着本来就有的渐强和渐弱,这些正是演奏者要不断重新创造的。单调的或者没有起伏的音乐对他来说是无法承受的,几乎要使他发疯。为了发现每一乐句的自然的形状,他发展出了一种慢动作的教学技巧。他会拿出巴赫的一首舞曲性的乐章首先是用慢动作以技巧上的惊人的完美来展示出句法和奏出乐句高低两端的音所需要的那种清晰性。然后他会显示需要渐弱到什么程度才能把后面的一个音符完美清晰地奏出。通后他用正常的速度来演奏这首乐曲,可以听到他如何用最自然的方法把所有这些美妙的细节结合起来。这就像用慢速度放映的电影可以发现用正常速度放映时注意不到的动作的奇妙部分。
有了卡萨尔斯的这种教学方法会导致情绪与技巧的必然结合。在讲了几分钟就能说明的有关技巧的问题之后,他越来越多地专注和陶醉于他正在演奏听乐曲中去,即使这首音乐曲他已经演奏过数千余次,他仍使自己完全沉浸于乐曲的激动的气氛之中。敏感和有接受能为的学生会理解到卡萨尔斯斯真正教的不仅是技巧、发音和乐句的结构,而且传授了罕见的可感觉到的激动人心的气氛。有时候卡萨尔斯会只用几句话来说明问题,但这些话是如此充满了激情,以致听起来这些话似乎是来自音乐本身似的。有时候他完全不用语言而是用演奏把全部这种感觉带到他的教学中来,这就成了一次演奏的生动体验了。在这一方面,我特别记起了他教舒曼的大提琴协奏曲时的情景。舒曼是在去世前不久创作这首协奏曲的,那时他的神经差不多已经错乱了。克拉拉·舒曼甚至回忆起作曲家把谱写这首协奏曲作为躲进在他的头脑中出现的天使与恶魔的一种办法。所有这一切可怕的遭遇全都写入这首协奏曲之中。我记得卡萨尔斯在那些零星的忽隐忽现的乐句在末乐章出现时说,疯狂正在到来,或者在演奏或谈论第一乐章时,他这样喊道:痛苦啊,痛苦—可怜的人,他是多么痛苦,他的弓子是那样地在琴弦上乱砍,他是深深地陷入在人的经历和艺术的体较感化而成的一种感情中去了。
对卡萨尔斯来说这是千真万确的。成绩的大小是和学生或艺术家的心理和生理上的成熟程度有关的。有些人是容易接受他提供给她们的东西,能够对他的教学作出反应和抓住他所教的东西。另外的一些,他们的见解还不成熟,需要很努力地去消化教给他们的东西,所以是不能在一堂课的时间里来评价其成绩的。在大部分专家大课上,学生只演奏一次或两次,所以很准对最后的结论作出评价。但是有才能和有接受能力的学生是能有重大的和立竿见影的改变,特别是在揉弦这类问题上。根据桑多尔·维(Sandor Vegh)的现察,在大部分音乐中是有一种基础音Grund-ton(是声音标准和质量前一种主要基础),它主要是平静的。对即使在必要时能够发展成为怒吼的音乐,卡萨尔斯也是用声音的这种清澈和纯净来开始的。但是当一个学生在演奏一首主要是朴素和平静的作品时使用了人们在高潮时—如在《特里斯坦》(Tristan)—所用的那种颤音的话,卡萨尔斯会立刻打断他说,这是一首朴素的田园风格的作品,你的颤音太快了,与这首作品是完全不协调的。如果这个学生很敏感和具备做出卡萨尔斯所要求的东西的技术能力,那他的改进是巨大的。原来听起来几乎是歇斯底里的东西第一次变得纯正了,去观察这种变化是很值得的。
虽然他有钢铁般的性格,但他是一个慈祥的人,他要让给他演奏的学生感到自由自在。可是他也是一个有脾气的人。大部分时间他是很和善的,他对待和他一起工作的艺术家是很热情的。有时候他去参加管弦乐队排练,在开始指挥之前,他会拥抱六个、八个、甚至二十个乐队成员,这是很感人也是很真诚的。这不是伤感而是一种感情上的真实,在目前比较冷酷的世界上这是很少有的。
另一方面,他作为一个大提琴家,他期望与要求有非常好的音准。不好的音准会使他非常烦乱。当他听到走调时几乎会在生理上感到恼怒—他会露出怒容,甚至会跺脚,对那些来见这位:大师时已经吓得发抖的学生来说,他是相当可怕的。二.有时他甚至会对管弦乐队大声呼喊:气我是一个烦人的老头;’可是这种情况是很罕见的。当然,他那暴风雨般的性格是在演奏大提琴时才显示出来,他为人热情和慷慨大方。
他两方面都用。他既在大提琴上极好地示范,但确实也用语言来很好地说明问题。有一些演奏家主要是靠本能来演奏的,要他们用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是有极大的困难的。这并投有什么贬低他们的艺术成就的意思,因为大部分音乐—正如卡萨尔斯经常说的——都是本能的。但是在他的班上和在管弦乐队里,甚至在他的晚年,他用语言来表达的能力是惊人的。
他不断地谈到那种他称之为音乐的法则或自然的法则的东西。例如:当音符在音高上向上进行时应该渐强。相反地,音符下行时应该渐弱。这种说法听起来也许过分简单化了,但是当人们听到他在巴赫的一个乐章中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的层次,这一切就变得多么自然和必要,人们会理解到这不是一种那么简单的概念。
另外一种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渐弱的性质。他会说,渐弱是音乐的生命,它使发音生动鲜明。在一个长音后面接着是一个短音,如果在长音上有一个渐弱,听起来就会更加清楚。或者有一些重复的音符,如果在第一个音符上有一个渐弱,那第二个音符就会听得更加清楚。他会把这类事情分别讲得很清楚,不过总是按照它们音乐上的前后关系来说的。如若没有充分的理由,他从来也不会提出一条拇指规则来的。也就是他的明确的表达能力才使我有可能写出《卡萨尔斯与表演艺术》一书。要把卡萨尔斯这样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的天才全都解释清楚是不可能的,我冒险地去写这本书是试图为后代把他大部分的原则保存下来。
我写这本书不完全是为了大提琴家的,虽然其中有许多关于弦乐演奏员值得花时间去研究的学识。但是它也为音乐家们写了有关音乐的一些原则。有一半以上的音乐例子—总数大约超过三百五十例—是引自卡萨尔斯指挥过的优秀管弦乐曲目;其余的是引自大提琴曲目。这传达了卡萨尔斯关于创造音乐的主要原则。
卡萨尔斯对许多在音乐上和私人关系上接近他的音乐家—也有非专业音乐家—最大的影响是解放了我们的感情,使我们不会不好意思去表达这种感情,他还给我们自豪感和鼓励我们去承认我们所爱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他有一种全面的感觉,使他能以最好的艺术趣味尽情地把感情放进音乐中去。最使我怀念卡萨尔斯,也是对我影响最大、最深的也正是他的光明磊落和他的演奏的宏亮声音的清彻透明。我敢肯定,所有听过他演奏或向他学习过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