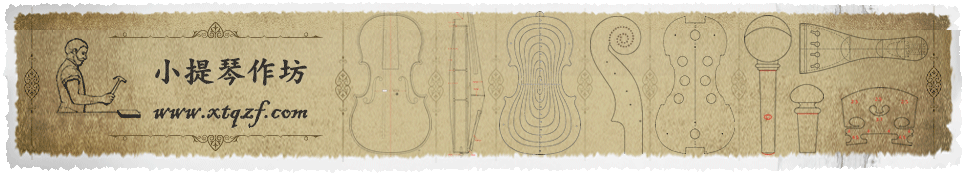被上帝收回的天籁琴音 杰奎琳·杜普蕾
 杰奎琳·杜普蕾
杰奎琳·杜普蕾
杰奎琳·杜普蕾(Jacqueline Mary du Pré)1945年1月26日出生于牛津的杰奎琳·杜普蕾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母亲爱芮丝是位钢琴家。爱芮丝曾在瑞士儿童音乐教育家达克罗兹的学校念书,取分教师证书后又赴伦敦的皇家音乐院进修;在遇见丈夫德瑞克之前,她的生活是朝着职业钢琴家的方向前进的,婚后却将心力全数转向家庭与孩子。
杜普蕾还不会说话,就已经可以准确的哼出歌曲的调调,而她的姊姊希拉蕊、弟弟皮尔斯也显现出音乐天份,母亲的欣喜可想而知。四岁时,小杜普蕾自收音机里的儿童音乐节目听到了大提琴的声音,她告诉妈妈:「我要一个“那个东西”」。母亲给了她一把成人尺寸的大提琴,亲自教她拉琴;每晚在孩子们就寝后,妈妈会谱出一首首新的小曲,在旁画上可爱的插图,摆在孩子床头,小杜普蕾每日醒来就可发现新的歌曲,实在令她期待极了。五岁时,杜普蕾进入伦敦大提琴学校,开始正式的大提琴课程,老师给她一把儿童尺寸的小琴,好强的她为此可闷闷不乐了一阵子。杜普蕾开始赢得许多小比赛,积极的母亲至此确定女儿有着极佳的天份,或许是因为自己成为钢琴家的梦想未能实现,爱芮丝决定倾全力发展女儿的音乐生涯。
封闭的神童生涯
十岁时,杜普蕾开始和名师普利兹(William Pleeth,1916-1999)学琴,自第一堂课起,普利兹就知道眼前的小女孩有着惊人的天赋,而在接下来的课程里,源源不绝地涌现。未久,他推荐杜普蕾参加苏姬雅奖学金(Suggia Gift)甄选,在座的评审包括了指挥家巴毕罗里(Sir John Barbirolli,1899-1970);本身即为大提琴家的他,被这位金发小女孩演奏时所散发的热力给震慑了,数分钟之后就决定将奖学金颁给杜普蕾,后来对她的演奏生涯更多所提携。有了苏姬雅奖学金的帮助,杜普蕾得以以每周两节课的速度,在伦敦的Guildhall音乐与戏剧学校继续和普利兹学琴;基金会更要求她每日课余,最少必须有四小时的练习时间。当时的学校同意让她免修一些课程,随着她音乐学习和演奏事业的起飞,一般的学校教育就愈被忽视;中学时期,为了要找到能配合她的学校,转了几次学,母亲甚至和学校摆明,女儿将不会参加中学会考或升学。
杜普蕾的母亲和全家就这样正式展开了神童的培训生活。家里有个神童,对每一成员而言都是耗尽心力的事;杜普蕾三姐弟都学音乐,姐姐的才华据说并不输她,但只有一人能受到全心的照顾。光是每天往返学校、家里、琴课的接送就十分繁重,更别提其余的杂事了,何况从学琴开始,母亲就一直担任杜普蕾的伴奏,演出比赛均不例外。并未接受完整基本教育的杜普蕾,对大提琴之外的世界可说一无所知,和同学们也欠缺正常的互动;也因为这样,个性害羞的她,对感情的需求极端强烈,却也缺乏安全感。英国人拘谨有礼的教育,教导她用微笑来掩饰一切不安,但没有了大提琴,他便很难与外界沟通。
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代言人
1960年,杜普蕾负笈瑞士的Zermatt,参加卡萨尔斯的大师班;15岁的她,还反叛性地挑剔大师的指导呢!两年后她又到了巴黎,接受托特里耶(Paul Tortelier,1914-1990)短期的指导;1966年更赴苏联和罗斯托波维奇学琴。她在莫斯科待了一个学期,适逢当年的柴可夫斯基大赛,罗斯托波维奇建议她参赛,但杜普蕾却觉得从观众席上去见识其他同辈的演奏,可比自己参赛要有趣多了。虽然曾和众多大师学习过,杜普蕾却执着地认为,普利兹才是她唯一的老师,是她的「大提琴爹地」。
英国的年轻音乐家们,向来都将在伦敦威格摩尔大厅(Wigmore Hall)的首次独奏会,视为最重要的踏脚石;如能获得好成绩,对事业的发展就大有帮助。1961年,16岁的杜普蕾举行了第一次威格摩尔厅的独奏会,普利兹为她规划了一个吃重的曲目,希望能充分展示她的能力;她的教母霍兰夫人更安排了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名琴供她使用。就在开始演奏第一首曲子之后没几分钟,琴上的A弦竟然逐渐变松,音越来越低;杜普蕾没被吓到,她先是镇静地调整自己手指的把位,尽力维持音准,直到弦实在松脱到不行了,方才站起向观众致歉,返回后台换上新弦。这个小插曲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她的演出,杜普蕾天生的舞台魅力,和异于一般英国音乐家的热情,为她赢得众多好评,演奏邀约马上如雪片般飞来。翌年,她在皇家节庆厅(Royal Festival Hall)和BBC交响乐团,演出了艾尔加(Edward Elgar,1857-1934)的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杜普蕾的诠释,有着满腔的热情、惆怅及孤寂,这首协奏曲,此后就和她的名字画上了等号。有趣的是,这并不是她本身最喜欢的大提琴协奏曲,却毫无疑问是她最常演奏的曲子。二十岁那年,杜普蕾和一路提携她的巴毕罗里合作,灌录了这首协奏曲,将她的国际名声更往上推进。

杜普蕾与巴伦波因
和许多神童一样,在迈入成人的交界时分,杜普蕾也曾陷入恐慌。乐评家和观众不再以儿童的标准去欣赏她的音乐,要求自然更严苛。虽然在表面上,乐评家一如往常地赞扬她的演出,杜普蕾却对长期以来的封闭生活厌倦了;她怀疑自己身为大提琴家的能力,却不知除了大提琴,她还能做什么。内心的冲突矛盾,加上各国巡演的孤寂和疲累,杜普蕾将大提琴摆在一旁,碰都不碰,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她明了自己所缺乏的一般教育,更羡幕平淡的生活,幸而她最后确定,自己是要成为大提琴家的。
1966年底,杜普蕾在华裔钢琴家傅聪的伦敦寓所里,认识了另一位音乐神童,来自阿根廷的犹太裔钢琴家兼指挥家巴伦波因(Daniel Barenboim,1942-)。两人在这次会面前,都才因感染了线热病而卧床;巴伦波因向朋友抱怨身体的不适,没想到朋友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糟,你应该去看看杰奎琳·杜普蕾,那才真叫严重呢!」。急于交换生病心得的巴伦波因,还真的打电话给杜普蕾,在电话里聊得相当投契,也因此在傅聪家的会面后,很快地展开了一段罗曼史。在精力充沛、豪爽好客的巴伦波因身旁,杜普蕾是个典型的小女人,一切以他的意见为主;高挑的杜普蕾为了掩饰两人在身高上大约13公分的差距,不仅将高跟鞋束之高阁,走路还刻意稍微驼一点。这段天雷勾动地火的感情,在几周之内就燃烧起来,善于组织安排的巴伦波因开始插手杜普蕾的演奏行程;除了早先安排好的邀约之外,两人尽量将演奏行程排在一起,可谓是形影不离。媒体对于这对金童玉女的恋情,也保持高度的关注。
以夫为贵
这对黄金组合的首次公开演奏是在1967年的3月,演奏了贝多芬和布拉姆斯的奏鸣曲;4月份则是由巴伦波因指挥英国室内管弦乐团,杜普蕾独奏演出海登的C大调大提琴协奏曲。两人演奏时的默契,像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很快地他们就对外宣布订婚的消息,婚期暂定当年九月。虽是在阿根廷出生,巴伦波因幼年便随父母移居以色列,杜普蕾为了与他共结连理,决定改信犹太教,成为犹太人。这对于英国中产阶级,笃信基督教的杜普蕾家来说,可谓是晴天霹雳;杜普蕾父母就曾告诉她,除了音乐之外,其他事都不要跟她的老师普利兹讲,因为他也是犹太人。被爱情冲昏头的杜普蕾,却是不顾一切地想融入巴伦波因的世界。当年五月,以色列爆发「六日战争」的前夕,心系祖国的巴伦波因取消在英国的音乐会,赶赴特拉维夫,杜普蕾自然也相随在侧。两人马不停蹄,以音乐作为媒介,在以色列各地演出,每天都有音乐会;在英国的杜普蕾家人和经纪人,却对她的安危担心不已。6月10日,战争胜利,以色列举国为之欢腾,在热情的气氛催化下,杜普蕾和巴伦波因决定将婚期提前,当场在以色列举行婚礼。五天后,杜普蕾成为巴伦波因夫人;虽对女儿改信犹太教感到不悦,杜普蕾父母依旧排除万难,从英国飞来参加婚礼。当时正好在以色列演出的巴毕罗里,也盛逢其会,婚宴上真是冠盖云集,连以色列总理都来祝贺。
金童玉女的婚姻,总是被外界蒙上一层浪漫的面纱,乐界将他们比喻为二十世纪的舒曼与克拉拉,殊不知褪下舞台的光环后,巴伦波因和杜普蕾也和你我一样,有平凡的夫妻生活要过。杜普蕾最向往的,并不是成为世界上最火红的大提琴家,而是享受平凡宁静的家庭生活。巴伦波因则是充满冲力,演奏行程排得满满,就算没有演出,家里也总是高朋满座。交往之初,他就着手替两人的事业做了规划,夫妻俩的生活,几乎都是在世界各地的机场、旅馆、音乐厅之间打转;杜普蕾纵使不情愿,还是得履行演奏合约。她的体力与精神,渐渐地到达了极限。
病魔的降临
大约在1970年前后,杜普蕾开始时常感到疲累,似乎全身的力气会在一瞬间消失殆尽,手指也出现了麻木的现象;她将之归罪于忙碌的演出行程,甚至责备自己的精神耗弱。1971到72年间,她从舞台上短暂消失,经纪公司对外宣称她因健康因素需要休长假。这段期间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有次杜普蕾连续几天都异常的有活力,以为自己已经复原了的她,和巴伦波因高兴地跑到录音室,花了两天的时间,录下了肖邦与法朗克的大提琴奏鸣曲。夫妻俩能再次共同演奏,激荡出的火花让他们兴奋不已,杜普蕾当场提议,不如趁胜来录些贝多芬吧!就当两人顺利录制完F大调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后,杜普蕾的精力却突然消失,将琴放回琴盒里,并表示:「就这样了」!甚至没有力气再听一下方才的录音成果;这是杜普蕾最终的录音。
她在1973年初复出,只是这时期的乐评就毁多于赞,人们认为天才的光环已经开始消逝。二月份,她在祖宾·梅塔(Zubin Mehta)的指挥下,演奏了艾尔加的协奏曲,这是她在伦敦最后一次的演出。几天后她飞到纽约准备和好友祖克曼(Pinchas Zukerman),由伯恩斯坦指挥与纽约爱乐演出布拉姆斯的复协奏曲。此时的她,连琴弓的重量都感觉不出来,更别提手指的灵活运用了;原先排定四场演奏,杜普蕾以「目视法」设法在指板上找出手指正确的位置,勉强演出了三场,这是她最后一次的公开演出。杜普蕾现在终于确定,是她的身体背叛了她;可是,没有人诊断得出来这是何种病症。
在杜普蕾短暂退隐的期间,她开始接受心理医师的治疗,随着不明病情的加重,她对心理医师的依赖就越重;出于自尊,许多时候她不愿对人提及自身的不适,甚至连丈夫都不知她的体力究竟衰退到什么地步。1973年十月,医师宣布她得了「多发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悬宕多时的病症终于有了实际的名称。简称为MS的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发生于中枢神经系统的疾病,侵袭患者的神经系统,导致肌肉失去强度及灵敏度,平衡会出现问题,甚至视觉、思考、说话都会受到影响,也就是俗称的「渐冻人」。潜伏期很长,急性发病期的间距可长可短,它不会传染,也不会致命,但是会影响患者的免疫系统,直到身体对其他病菌毫无招架之力为止。就因为MS常以不同的症状出现,早期极难判断,医学界至今仍不十分了解病因,也仍旧无法治愈。杜普蕾的诊断结果出笼时,巴伦波因正在以色列演奏,完全没概念的他和梅塔一同去请教当地的医师,得知这是不治之症后,他心急如焚地立刻飞回英国。这时的杜普蕾只有28岁,演奏生涯却提前结束了。
适应现实生活
杜普蕾的病程进展缓慢,除了服药做复健,她持续每周接受两次的心理治疗。自幼习惯以大提琴来表达内心的她,现在得学会借由语言、文字来表达自己,刚开始的确是一番挣扎。她还是尝试要拉大提琴,只是发出来的刺耳声音,反而加深了她的沮丧。巴伦波因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对妻子的患病给予最大的支持,演奏事业持续发烧中的他,每当杜普蕾发病或需要他的时候,就会取消演出赶回伦敦,只是在现实生活中,他又能取消多少音乐会呢?在居住环境方面,也得做调整,走路开始有问题的杜普蕾,起先坚持用臀部一阶一阶地下楼梯,只是当坐轮椅成为既定事实的时候,就必须考虑换房子了。当时的伦敦,无障碍设施还不普及,在住家环境的配合上更是困难。幸而杜普蕾的朋友,舞蹈家玛歌·芳婷(Margot Fonteyn,1919-1991)伸出了援手。芳婷的丈夫是位四肢麻痹的人,他们正欲将老房子脱手,里面的无障碍设施,包括电动升降梯,一应俱全。很快的,巴伦波因夫妇就搬进这栋新房子,也请了护士、管家来帮助家务。
此时的巴伦波因,是音乐界新兴的当红炸子鸡,纵有心陪伴患病的妻子,却无法将事业无限期的停摆下去。1974年他受邀担任巴黎管弦乐团的指挥,这样好的发展机会,巴伦波因虽心动,却顾虑着妻子的病情而陷入犹豫。合约要求他每年必须长驻巴黎20周,最后考虑到巴黎和伦敦距离并不太远,在杜普蕾的鼓励下,他接受了这份工作。喜欢有人陪伴的杜普蕾,除了每天等待巴伦波因的电话外,家里依然高朋满座,热闹得很。
走出封闭
生病之初,杜普蕾自然也经过一段消沉的日子,大提琴是她的生命,如今却无法再演奏,心里的不甘与愤怒可想而知。虽然肢体逐渐衰退僵硬,心灵却依旧活跃,她可以选择足不出户,也可以选择勇敢面对众人,以她的知名度为多发性硬化症招来关注。1975年10月,由芳婷夫人推着轮椅,杜普蕾出现在伦敦的柯芬园,这是她首次坐轮椅出现在公开场合;心防一旦突破,她也踏出了享受她剩下人生的第一步。1976年1月,杜普蕾获颁英国帝国勋章(OBE),也接受了BBC电视台的节目访问,坦诚讨论自己的病痛。当年七月,由巴伦波因推着她的轮椅,杜普蕾再度登上了艾伯特厅的舞台,以往常在此演奏的她,这回是在「玩具交响曲」里担任敲边鼓的工作,能再次参与现场音乐会的演出,她玩得不亦乐乎,观众在鼓掌叫好之余,恐怕也感到心酸。
杜普蕾的心理医师曾表示,她之所以日以继夜需要人陪伴,是因为音乐仍随时在她的脑海里盘旋,挥之不去;只有在有人陪伴之时,才能将她的心思转移到别处。就算在病中,她也不断揣测乐曲的诠释,但在卧病的头几年,她极少向人提及她的大提琴,只要一听到自己以前灌录的唱片,就难过得落泪。经过一段时日的逃避,她领悟到,这些唱片是她在音乐上的见证,听了这些录音,就彷佛置身当时的情景-她想要永远只听自己的录音。她开始教学生,因为教学也是间接的音乐创作,而且可以充实她的生活。起先她只收了少数几个学生,都是自己的好友,将自己对音乐的诠释尽情投射在学生的演奏上。1977年,杜普蕾在布来顿音乐节连续两日举办大师班,教授艾尔加的协奏曲,她起先虽有点犹豫,但在巴伦波因陪伴下,以口哨及唱歌的方式代替运弓,以目光来带领学生的动作,生动而清晰。大师班的成功,大大激励了她的精神,接下来的几年间,杜普蕾在多个音乐节都有大师班的课程,周末也在家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们举办迷你大师班。1979年,BBC电视台录制了四个钟头的大师班,在电视上播映,她全心投入教学,虽从未遇过天份与技巧兼具的奇葩,但教琴让她和音乐又有了直接的接触。
在琴音中辞世
1980年以后,杜普蕾的健康每况愈下,长期的病痛对她和巴伦波因都是艰难的考验,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巴伦波因每两周便会返回伦敦探望她,直到他在巴黎另组家庭为止。1982至86年间,杜普蕾的母亲和婆婆,还有一位挚友相继离世。除了僵硬的肢体,她的语言能力也愈来愈差,连视力都几乎不复存在。免疫力极差的她,陆续受到疾病感染,到最后连呼吸都很困难了。1987年的10月19日,她又感染了肺炎,巴伦波因从巴黎赶了回来,她的恩师普利兹也陪伴在侧;最了解她的大提琴爹地,选择了她自己深爱的舒曼大提琴协奏曲录音,杜普蕾就在自己的琴声中离世,享年42岁。
杜普蕾的家人
杜普蕾的母亲爱芮丝,早期和女儿形影不离,对她的生活学习各方面,掌握得滴水不露。本身是钢琴家的她,对于一位音乐神童的养成,比任何人都积极,更何况她的儿女都具有非凡的天赋;只是在有限的资源下,她选择将所有精力投注在二女儿身上,或许也不自觉地将年少时的梦想-成为钢琴演奏家-投射到女儿身上去完成。在塑造神童的过程中,她似乎是太过重视大提琴了;杜普蕾只接受了零星的正规学校教育,数学科学文学都欠缺基本概念,连大提琴以外的其他音乐知识她也十分贫乏。杜普蕾虽然得到家里最多的资源,却得不到她最需要的爱。
杜普蕾的父母,对她改信犹太教这件事,一直不甚谅解。她发病后,母女间的互动相当冷淡,按照常理,爱芮丝应该会仔细的照护生病的女儿才对啊!但据杜普蕾的管家、护士等人的回忆,她的家人很少去探望她,而且每次一来杜普蕾还会给她们钱。在70年代,一般人对多发性硬化症尚毫无所知的时候,不少人认为杜普蕾的患病,是她背叛了基督教的惩罚;或许杜普蕾的家人也是这么认为。也可能是因全家付出牺牲的太多,原以为杜普蕾的成就会如日中天,不料却杀出MS这个程咬金,一家人的重心与希望顿成泡影;愤怒与失望的情绪被转嫁到病人杜普蕾的身上,以致于不愿跟她有太多交集。
1997年,杜普蕾的姐姐希拉里和弟弟皮尔斯出版了一本书《家中的天才》(A Genius in the Family),随即被拍摄成商业电影《无情荒地有琴天》(Hilary and Jackie)。希拉里将自己塑造成被牺牲的可怜角色,杜普蕾则被塑造成任性骄纵的人,甚至要求希拉里将丈夫和她一起分享;电影一出,这段故事引起广泛讨论。但希拉里的大女儿很快地跳出来反驳,在她的记忆中,杜普蕾和姐夫Finzi的确有过一段为时大约一年的婚外情,但并不是杜普蕾自己主动,而是惯性外遇的Finzi,趁着杜普蕾和巴伦波因感情出现嫌隙时,趁机引诱小姨子的。真相到底为何,恐怕是说不清的了。
才子佳人的褪色婚姻
和她的演奏一样,杜普蕾的热力,极容易感染他人。她的个子很高,骨架也大,少女时期更是出了名的不会打扮;但是她的微笑与真诚直率,还是轻易地吸引了许多目光。除了少女时期青涩的恋情外,第一段正式的感情是钢琴家史蒂芬·毕夏普·柯瓦维契(Stephen Kovacevich,早期以Stephen Bishop名字出道)。两人在经纪公司的安排下,一起巡回演奏,是标准的日久生情;当时已婚的柯瓦维契,和杜普蕾搭档的二年半期间也与妻子离婚,但他们的感情却杀出另一号人物,钢琴家理查德·古德(Richard Goode),柯瓦维契后来曾与钢琴女王阿格丽希结婚。杜普蕾和古德的交往时间并不长,分手又复合了几次,之间始终都还存在着柯瓦维契这号人物。这两个男人在个性上和杜普蕾大相径庭,他们都很沉静,善于分析,或许就是吸引杜普蕾的理由。直到她遇见巴伦波因。杜普蕾刚过世的数年间,巴伦波因被塑造成一个负心汉,其实不尽公平。他们的婚姻刚开始固然甜蜜,但个性上的南辕北辙早就造成了冲突。巴伦波因对事业野心勃勃,善于交际组织,家里杂事也是他一手包办;杜普蕾其实并不喜欢四处巡演的生活,相当害羞不易与人亲近,对于大提琴以外的各类杂事更是一窍不通。如果杜普蕾与姐夫的婚外情属实,她与巴伦波因的感情早出现裂痕;发病后,长期照顾病人的压力,加上因事业发展的聚少离多,两人的关系倒是跌破众人眼镜的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虽然两人后来终究形同陌路,直到杜普蕾去世为止,巴伦波因都和她维持着婚姻关系,在巴黎的新家庭也始终瞒着她,生活经济上的照料更是从未停止。在西方社会,尤其是浪漫成性的音乐圈里,巴伦波因对杜普蕾的用心已属难得。才子佳人的褪色婚姻,只能说是造化弄人吧!
杜普蕾的音乐
提起杜普蕾,脑海里马上浮现她那一头长长的金发,丰富的肢体语言摆动。她是个直觉型的演奏家,内心的情感随着音乐流泄出来,总能准确的抓到音乐的精髓。打从孩提时代的小小演出,就有人对她夸张的肢体动作加以批评,然而这些动作并不是为了增加效果而设计出来的,仔细观察就可发现她都是随着音乐的走向在摆动。她的身材高大,十分适合拉大提琴,技巧也相当出色;不过最吸引人的,还是那完全不受约束、毫无保留的热情,每一个音都是发自她的心底。杜普蕾演奏乐曲的速度比起一般人是偏慢的,但她有惊人的能力将冗长乐句的张力维持不坠。
杜普蕾的曲目乍看之下不算太广,实际上对26、7岁就停止演奏的她来说,已属上乘,若她的事业能再持续下去,或许就会演出更多不同的乐曲。目前市面上所能见到的录音,几乎都是最普遍常见的大提琴曲目,除了艾尔加之外,差不多就是德弗札克、舒曼等协奏曲,她并未演奏太古典和太现代的乐曲。她很喜欢室内乐,除了和巴伦波因合奏的奏鸣曲之外,也享受与好友如祖克曼等人拉奏室内乐的时光。不过巴伦波因就曾表示,无论是指挥或是弹钢琴,帮杜普蕾伴奏都不是件简单的事;她有一种浑然天成的节奏,速度上的变化极有弹性,但由于这些都是发自她的直觉,她并不知道这对于伴奏的人来说是很难跟上的。也幸好她有巴伦波因!从夫妻俩和祖克曼合作的贝多芬《幽灵》三重奏之中,可以听见钢琴和大提琴那几乎是一体成型、天衣无缝的演奏,音乐中好像只有他俩,祖克曼稍稍地被排在他们的世界之外了。
 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 1712年「Davidoff」
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 1712年「Davidoff」
名琴陪衬,相得益彰
而一把好琴,能使好的音乐家如虎添翼。小时候曾使用过瓜奈里、卢杰利和Tecchler这些高等级的大提琴,全是她教母霍兰夫人送她的。1961年的威格摩尔厅演奏会时,使用的是1673年的斯特拉迪瓦里;三年后,霍兰夫人听闻著名的「戴维朵夫(Davidoff)」斯特拉迪瓦里要出售,便请人带到伦敦让杜普蕾试奏。「戴维朵夫」可称得上是斯特拉迪瓦里大提琴中的极品,音色温润却有极强的穿透力,对于时常为音量所苦的大提琴家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好琴,杜普蕾自然爱不释手,霍兰夫人便将它买下供杜普蕾使用。她和巴毕罗里的艾尔加协奏曲的录音里,使用的便是这把琴。1968年,她又获得一把Goffriller名琴,也用它录了几次音。
「戴维朵夫」和Goffriller的声音质量都相当清澈优美,反应也很敏感,但杜普蕾强烈的演奏方式,不仅使得琴需要时常的调整,在与乐团合奏需要强大音量的场合,这两把琴似乎就不够勇健。1970年,巴伦波因听到好友祖克曼演奏一把由美国费城制琴师佩雷森(Sergio Peresson)所制的小提琴,激赏不已,马上请他为妻子打造一把大提琴。杜普蕾果然对这把琴赞不绝口,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巡回世界各地,使用的都是这把佩雷森大提琴。
留存下来的影音纪录
舒曼大提琴协奏曲的录音,据说是杜普蕾自己最喜欢的。舒曼的协奏曲充满了冲突、犹豫、矛盾和柔情,而杜普蕾的演奏音色变化细腻,随着音乐娓娓道出内心的感情转折,时而奔放,时而愤怒,将这首曲子的多变掌握得淋漓尽致。至于大家所熟悉的艾尔加协奏曲,杜普蕾曾于1965年与1970年录制过两次,第一次是由巴毕罗里指挥伦敦交响乐团,五年后则是与巴伦波因及费城管弦乐团合作。巴毕罗里曾在场聆听这曲子的首演,更曾以大提琴独奏家的身分演出,对乐曲各部细节的掌握可说游刃有余;当时只有20岁的杜普蕾,竟能将乐曲中的沉痛与惆怅全然表达出来,似乎这曲子和她的灵魂深处有种难以言喻的交集。可是当杜普蕾第一次听到这个众人称赞的录音时,眼泪不禁落了下来,因为「这不是我所想要表达的意思!」和巴伦波因的录音,则是热情澎湃,充满愉悦。
关于杜普蕾的书,除了前述拍成电影的书之外,尚有伊丝顿(Carol Easton)所著的《大提琴的爱与死》(现已绝版),还有她的学生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在巴伦波因协助下完成的《杜普蕾的爱恨生死》。书中立场各有不同,但均对杜普蕾的人生做了一番详细的介绍。由于杜普蕾当红的年代,正是电视媒介起飞的时候,英国纪录片导演纽朋(Christopher Nupen)尝试以生活化的方式,人性化地描绘音乐家们。于公于私,他和杜普蕾都是好友,他一共拍了三部纪录片《Remembering Jacqueline Du Pré 》、《Jacqueline Du Pré in Portrait》及《The Trout》。在《鳟鱼》这部片里,记录着新婚燕尔的杜普蕾夫妇,和「巴伦波因帮」的成员帕尔曼、祖克曼、难得以低音提琴家身分出现的梅塔,在英国排练演出舒伯特《鳟鱼》五重奏的情景,年轻而才华洋溢的一群人,活力简直可以感染镜头之外的观众。第二部收录了她与巴伦波因演出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以及加入了祖克曼的《幽灵》三重奏;纽朋后来又征得她的同意,在她患病后又拍了一段纪录片,有她指导学生的片段。从镜头里可以看到她不太清楚的话语,以及刻意用右手遮掩住,已经会不由自主抖动的左手,令人不胜唏嘘。
上帝将杜普蕾送到人世间,让她以她的大提琴打动人心,却又迅速的将这份礼物收回,留下的,是她最精华年代的音乐,永远萦绕在人们的脑海里。